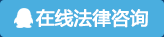近日,辽宁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发布《辽宁省公安机关办理收容教育案件规定》,规定14类卖淫嫖娼人员,将不予收容教育(11月15日《辽宁日报》)。尽管也有评论者认为它“体现法治进步”,但笔者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欣慰,相反却为收容教育的大行其道感到郁闷,因为在笔者看来,收容教育该寿终正寝了。
收容教育,是指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收容教育的直接法律依据是,1993年9月4日国务院颁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而国务院的这个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则是,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该《决定》规定,对卖淫、嫖娼的,除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外,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很显然,这是一个授权立法条款,将规范收容教育的立法权授予了国务院。
那么,收容教育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处理行为呢,它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行政处罚?从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规定看,它是一种“行政强制教育措施”,而从它的设立目的、决定机关和执行方式看,它与目前的劳动教养有更多的相似性,且收容教育也不是为促使当事人履行某种法定义务而采取的中间措施,因此,它更像行政处罚。但不管行政强制措施也好,行政处罚也好,收容教育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长期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且这种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理既不用检察机关审查,又无须法院作出裁决,公安机关自身就可以决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强烈质疑收容教育的合法性,认为它也该寿终正寝了,应明确予以废止。
首先,收容教育与我国法治进步趋势和人权保障要求相悖。从法治要求看,任何人不经合法设立的法庭裁判,不得认定犯罪,执行刑罚。虽然收容教育不是刑罚措施,但它对当事人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度与执行刑罚并无实质差别,所执行的期限比一些轻微犯罪判处的刑罚还要长。然而,这种比刑事处罚还要严厉的所谓“行政强制教育措施”却可以不经过法律而只由公安机关决定即可。这不仅与现代法治的要求相距甚远,也违反我国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根本要求。
事实上,从我国法治进步的趋势看,“收容类”强制措施和处罚是逐步取消的,而不是相反。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收容教育的类似系列措施主要包括收容审查、收容遣送和劳动教养。收容审查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在1997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已经明确废除。而收容遣送也于2003年的强烈谴责和质疑声中落幕。至于劳动教养虽未被明确废除,但有两点却预示着它的存在也不会太长久了,一是我国正在制定违法行为矫正法,拟取代劳动教养制度,二是今年3月正式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已经剔除了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
其次,从立法进程及其蕴含的法律精神看,收容教育的最初法律依据已经被否定,失去了合法性。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规定了收容教育,而1994年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规定卖淫嫖娼处罚时却没有把收容教育纳入其中,按照法律适用上的新法优于旧法原则,这意味着收容教育已经被否定。而颇为让人不解的是,1997年修改刑法时,却笼统地肯定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规定中的行政处罚规定,使收容教育得以保留下来,这显然是一种立法疏忽,结果造成了法律规定的前后矛盾。
更为滑稽的是,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今年3月1日刚刚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规定收容教育问题上,与此前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均有不同。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有本法第六十七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第六十八条(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第七十条(为赌博提供条件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而对卖淫嫖娼却没有规定可以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这至少可以说明对卖淫嫖娼不适用收容教育了。
最后,收容教育法规所依据的法律授权违背立法法的规定,正当性和合法性全失,应属被清理和禁止之列。2000年生效的《立法法》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并未授权给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这说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将规定收容教育这种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立法权授予国务院,在9年后已经失去了它的合法性,该授权应当终止,依据授予制定的相关法规应当立法失效。
总之,收容教育是我国目前除了劳动教养外的一项可以不经过法律而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两年的制度,无论从人权保障要求,还是从我国法治进步趋势及实际立法进程看,它都存在明显的违法性和非正当性,应当尽快予以废除,让它寿终正寝。